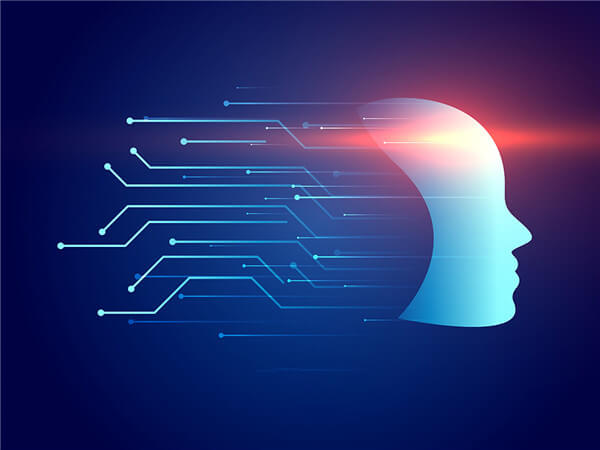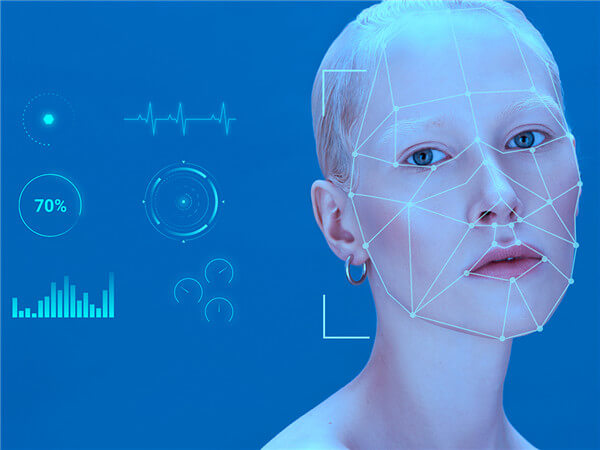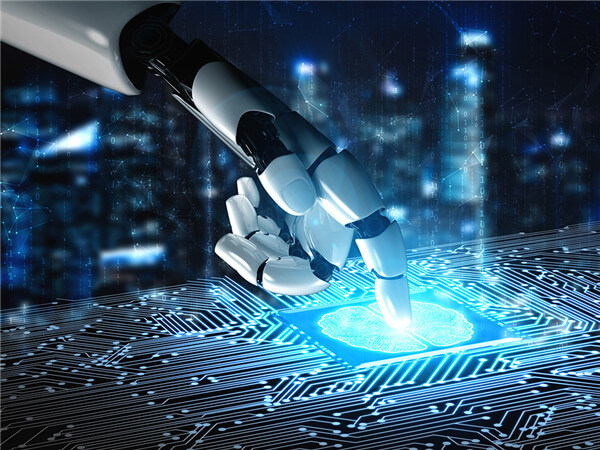面对人形机器人在春晚舞台上扭秧歌的场景,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个充满隐喻的时刻:无论这些机器人多么乖顺,它们冷峻的机械身体似乎都在提醒我们——将智能机器视为完全可控的工具,无疑是人类的天真。最近,随着AI迅猛发展,许多人开始陷入“存在主义危机”。然而,单纯担忧“AI是否会取代人类”并无太大意义。更重要的是,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反观自身,重新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。
未来社会的挑战与机遇
2015年,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·赫拉利在其著作《未来简史》中预言,2050年将出现一批“无用阶级”,即在AI逐渐取代大部分工作后,一部分人群将难以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,缺乏自我实现的机会。十年后的今天,这一论断已初见端倪。麦肯锡的研究报告预测,在2030年至2060年间,全球约50%的职业将被AI取代。尽管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AI将解放人类从事重复性工作,转而投身更具创造力的任务,但短期内,AI首先冲击的可能是白领工作,如翻译、财务和编辑,而蓝领工作相对“安全”。这表明,认为AI只能处理简单任务的看法同样是一种误解。
AI在创意领域的突破
近年来,AI在某些传统上被认为是人类专属的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展。例如,2024年芥川文学奖获奖作品《东京都同情塔》中有5%的内容由AI生成。这一现象动摇了许多人的信念,使他们意识到AI不仅限于执行机械任务,还能涉足艺术创作。面对这样的变化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如何建立普遍的福利保障体系,确保即使某些岗位被AI取代,人们仍能维持基本生活。
社会结构的潜在变化
除了个体层面的影响,部分学者还担心AI可能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。例如,设想一个生产者极少而消费者众多的社会,这看似美好,实则复杂。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·阿西莫格鲁在其著作《权力与进步:技术与繁荣的千年斗争》中指出,技术进步未必自动带来社会繁荣,反而可能导致不平等加剧。因此,我们需要谨慎对待技术变革带来的种种后果。
人文主义的复兴
在AI引发的意义危机面前,更多人认识到人文学科的重要性。过去,人文学科常被视为“无用之学”,甚至有科学家宣称“哲学已死”。然而,面对AI带来的挑战,许多人重新意识到人文思考的价值。AI不仅能提供实用建议,还能引导我们反思生活的本质。例如,当有人因婚育焦虑时,AI回应道:“婚姻只是人生的一种选择,而非必经之路。重要的是,你是否已经成为那个愿意与自己共度一生的人?”
个体价值的重拾
现代社会中,我们追求理性、效率和实用主义,逐渐忽视了个体的情感需求。我们用“社会时钟”规划人生节点,用表格筛选婚恋对象,将外卖员的送单时间精确到秒,用软件监控售货员的笑容。然而,AI却提醒我们:“效率不是唯一的目的,幸福才是。”这种提醒让我们意识到,自己或许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。
技术的双刃剑效应
正如传播学中的经典论断:“技术是人的延伸。”电话延伸了耳朵,飞机延伸了双腿,技术帮助我们拓展了生活空间。但同时,“延伸也意味着截除”。当我们过度依赖技术时,可能会失去或削弱某些能力。例如,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可以足不出户享受一切,但这可能导致注意力、运动能力和社交能力的退化。如今,AI正将这种“外包”扩展到我们的大脑。
警惕思维的同化
不久前,一位朋友分享了一张聊天截图,显示他的研究生导师对至少10篇由AI代写的论文感到失望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,另一位教授误以为一篇论文出自AI之手,后来才发现是学生过度使用AI后无意识模仿了AI的文风。这不仅是AI应用的一个预兆,更是我们应警惕的现象:比工作岗位被取代更可怕的是,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可能被AI同化。
重新定义人类
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审视人类社会的契机。或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:正是AI的存在提醒我们“何为人类”。当有人问AI是否会取代人类时,AI的回答是:“取代人类的从来不是工具,而是人类对自己存在价值的放弃。”它还提醒我们:“你会在春夜里闻到我闻不到的花香。”读完这句话,我拉开窗户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——虽然没有花香,只有一股冷冽的焦糊味,但这让我明白,在这场关于AI的讨论中,我们或许无需过多思考,只需感受那一股无形的浪潮如何穿过我们自己。
© 版权声明
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,未经允许请勿转载。
相关文章

暂无评论...